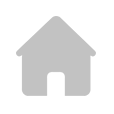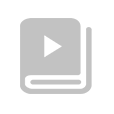本文所论述的隐秘与启蒙问题,简而言之是真理能否向所有人公开,与在
说出真理时应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隐秘与启蒙分别指称真理的暗示方法和明示
方法。这一问题对真理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个与其内容无关的外部问题,也非仅仅与
言说真理者的个体性情有关的风格问题,相反,它在某种意义上源自真理本身
的某种特质和需要。其次,真理与人类福祉息息有关,真理使人自由,但真
理也包括着巨大的危险,假如言说真理的机会不
当或形式不对,就可能酿成没办法估量的灾祸。因此,深入讨论这一问题有可
能使人在这一年代获得对于真理负面效应的免疫力,并促进思想者采取符合年代
情况的真理言说样式。
本文的讨论由此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对真理迄今为止的各种文本形式进行
修辞剖析;第二是论证真理因为其危险性不适合向所有人公开;最后,我将展望在
启蒙现代性中回到隐秘传统的可能性和限度。
真理形式的谱系本文所称真理,专指对作为社会基础的规范规则和人性倾向
的剖析、质疑或辩护所形成的命题,通常来讲即是针对现存秩序的价值评判体系
及其衍生规制的深层考虑,与在此基础上对于人性提出的建构性的需要。价值
中立的社会科学(姑且假定它做到了这一点)和无涉价值的自然科学(我不不承认
它会引发社会和政治问题)命题不是本文讨论的真理范围。如此,传统意义上
的人文学科中包括伦理和政治关怀的命题便成为本文所要考量的对象。毫无疑问,
这样界定的真理定义甚至不可以与错误不同开来,如此本文所谓的真理毋宁说是
“真理理解”,但本文的重点并不在真理的可错性。实质上,真理对于人世的影
响更多地不是因为它的可错性,而是因为它让人言讲出的方法,一种平和的错
误思想比一种激烈的正确思想给人世导致的害处要小得多。
如此界定的真理可按其来源近似地划分为希腊式真理和希伯莱式真理,前者
在本文中指称哲学和政治思想,亦即整个苏格拉底传统;后者指称从最高者出发
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亦即从《圣经》衍生的犹太- 基督教思想传统。这两种真
理有什么区别并不在于前者是只关心抽象法则的死的真理而后者是关怀人的期望和拯
救的活的真理,而在于两种不一样的对个体生命意义及社会秩序正当性来源的理解
的紧张;希腊真理是在哲学家的可朽肉身上打造起来的不朽城邦,而希伯莱真理
是自然性身体空出地方后承纳的属灵的身体。对二者的比较将在另外的文章里进
行,本文主要关心真理与政治社会或现实城邦之间的关联,因此注意力更多地放
在希腊式真理之上。下面分别对这种种真理的语言样态作一初步剖析。
第一个将暗示风格发挥到极致的是赫拉克利特,他的残篇向来被视为高深莫
测的秘密思想的典范。在他那里,对逻各斯和灵魂的言说以海量隐喻作出,这类
隐喻有火、水、虱子、儿童等等。根据海德格尔的解释说明,因为自然或逻各斯本身
就是在显现中隐藏自己的东西,逻各斯言说自己,人应合其言说方有所说,如此
赫氏文本的形式好像是其思想回到语言本身后的非此不可的内在需要。这在肯定
意义上是成立的,由于其残篇中有一条“德尔菲那位发神谕的大神即不说话,也
不沉默,而只不过(用符号)暗示”,这里的大神显然指称自然本身的一个维度
(好似海氏所谓天、地、人、神),而“符号”指称那种签文式的隐喻。赫拉克
利特住在神庙中,看上去是在诸神隐遁后仍然期待和守望神灵,他那充满暗示和激
发性的言说处处符合着自然本身和语言本身的特质,隐喻构成了语言、思想、自
然这三者之间的切近,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即是这隐喻本身。但从其次来看,
这种风格也与赫氏本人蔑视庸众的个体性情有关,他要使自己变得艰涩以与平时
言说的肤浅风格不同开来,从而形成某种言说方法的等级制,在这种等级制中,
只有出色的人才会用隐喻,而粗糙的灵魂对此是没办法领会也没办法效仿的。他的
简练和晦涩,正如尼采引用让- 保尔的话所言,乃是出于如此是什么原因:“大体而
言,假如所有伟大的事物——对于少数人心智有很多意义的事物——仅仅被简练
地并(因而)晦涩地表达出来,使得空虚的头脑宁肯把它讲解为胡言乱语,而不
是翻译为他们自己浅薄思想,那样这就对了。由于,俗人的头脑有一种可恶的技
能,就是在最深刻丰富的格言中,除去他们我们的平时俗见以外,便一无所见。”
(尼采《希腊悲剧年代的哲学》)
假如说赫拉克利特是诸神远遁后受人冷落的神庙,那样苏格拉底就是民主时
代万人云集的广场。赫拉克利特是虱子,大家看见并捉住的,大家把它放了,我
们看不见也未捉住的,大家把它携带;而苏格拉底是牛虻,叫人意识到自己的无
知。韦尔南《希腊思想的由来》详尽剖析了苏格拉底思想与希腊城邦几何学结构
之间的同构和生成关系。苏格拉底言说方法的特质,在于他的全部思想都在广场
的对话空间中依赖声音而形成和显现。他不用那种布道式的宣讲或独白语式,
他了解那只是真理从外部对别人的入侵,他期望在对话中叫人自己意识到自己
与真理的距离并重新接近。他甚至不需要文字把这类对话记录下来,可能是由于他
对真理的活的、当下的形成的执着,在这一空间中真理依赖声音的在场而得以维
系它的生命,真理源自平等的交流而引发的独立自由的探究,而文字不可防止
地包括着某种不平等的强制性及误解的可能。苏格拉底因为深知整体的神秘难解
和无知在某种程度上的宿命性质,从而极其珍视人性的自由,他在对话中从不武
断地下结论,也不强求共识。苏格拉底不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而是在大家每
个人心中回响的那个不断质疑、提问的孤立而顽强的声音。
苏格拉底之死带来了对话的终结。柏拉图开始了以写取代说、以对话录取代
对话的书写年代,亦即哲学年代。在这里,真理的成形不是在当下空间的自由论
辩和交流中发生,而要依赖对文字的理解引发的对原初声音的回忆。城邦空间隐
入了文本空间,现场性让坐落于回忆,质朴无华的对话让坐落于修辞的运用。应该说,
柏拉图使真理更能传之久远了,由于写比说更拥有在时间中的持存性。然而,由
于真理在对话中是活的、不断返回到它的原初状况的问题,而文字的固定性可能
使问题蜕变为答案从而失去它的鲜活性。文字依靠于观看,而声音依靠于倾听,
听比看更生动、更有直接性,听离事物更近。苏格拉底那里还存留着赫拉克利特
对逻各斯言说的听觉,而柏拉图把逻各斯变为理念,变成纯粹观照的产物。当然,
柏拉图对这类危险也有相当的自觉,他的对话录毕竟还是对话,虽然这种对话已
经隐入文本和内心;他对修辞的运用也是在深思哲学与政治社会的紧张后试图缓
解真理的负面效应的努力(见后面的论述)。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话录也消失了,只剩下了作者一个人的观念在文本中
说话。这种依据形式逻辑的范畴推演,这种独白性论述将所有些异在的话语全都
统摄在自己之内,用批判和逻辑线索将它们抛弃或并入自己,《形而上学》第一
卷中对前贤思想的列举看上去是一位织工在陈列他的织架。亚里士多德这里失去了
柏拉图的修辞,而多是学究式的质木无文的思辩。虽然这样,亚里士多德实质上
提出了“逻辑面前每人平等”这一思想戒条,从而确保了人有自主运用形式逻辑
质疑某种思想确当性的可能和自由,由于形式逻辑毕竟为人所共有。这种基于形
式逻辑的论辩和质疑在后来的经院哲学中成为最重要原则,使自由和平等成为“思
想共和制”的自然法。(见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
在轴心年代的另一极,在《旧约》中的《约伯记》、《诗篇》、《传道书》、
《雅歌》等伟大文本中,比喻手法得到了前所未有些运用和精致化,那种禀有神
性光辉的思想好像天生就适于用一种隐喻的形式表达出来。与赫拉克利特的隐喻
性思想(思想本身即隐喻)、柏拉图的运用隐喻的思想(一种严格的理性思想披
上隐喻的外衣使之隐藏起来)与亚里士多德的纯理性思想不同,希伯莱思想的
隐喻乃是作为一种象征出现。象征,按别尔嘉耶夫的说法,是“无限在有限中的
彰显”;在修辞学中,象征表明了事物的同一性和完整性,“一物是它所象征的
东西”。在这里,隐喻构成一个路标,一个指示记号,它指向无限,指示神与这
个世界的关联。而在赫拉克利特那里,隐喻仅仅表明与自我隐匿的自然相应的语
言本身的形式,这里的隐喻并不拥有那种明确的指向,而具备梦境般的多重歧义
性,故赫拉克利特的隐喻是修辞学上的寓言。
耶稣基督的到来使希伯莱的隐喻方法获得了最为集中和辉煌的展示与解释说明。
在福音书中,耶稣反复宣讲着盐、光、方法、果树、撒种、葡萄园、羊等比
喻,十字架本身就构成一个大的象征:言成了肉身,亦即属灵的身体来到自然性
身体之上。象征就是约,即自然性身体与属灵身体之间的契约。当基督说我们的
身体和血是面包和酒时,他说的不是“面包和酒”代表他的身体和血,而是说就
是身体和血,把这个“是”理解成“
代表“表明人不理解、不信。《马太福音》中耶稣回答了用比喻的因由:”
由于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了解,不叫他们了解,凡有些,还要加给他,叫他有
余;凡没的,连他所有些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
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知道。“这类话其实是针对那些以理智自居而不信的人
说的,他们不愿相信比喻,由于比喻实在是天国的方言,他们被经验和理性圈死
的头脑对这种方言是绝缘的。用比喻,是为了应付人的理智的自负,”进入天国
的门是窄的,而自负却把人变成庞然大物“。
摩西的诫条说:“不可妄称雅威的名。”那样神学,一种试图在思想中把握
上帝的努力该怎么样言说上帝?整个《新约》中众使徒和其他基督的仆人使用了一
种祈祷语式,在这一语式中,人不谈论上帝,人呼唤上帝。在传言基督的海量教
义时,他们不是居高临下地训戒人,而是同大家一块祈祷、为大家祈祷,甚至为
不信的大家祈祷。这一语式在奥古斯丁《忏悔录》表现得特别明显,奥古斯丁在
考虑时间问题时几乎是一唱三叹式地将荣耀和大能归结为主,他反复地从雄辩后
退,退向祈祷。祈祷语式此后渐渐传承,直到近期奥特《上帝》一书重申了神学
的这一特质。
当大家不再呼唤上帝而只是谈论上帝时,他在谈的就不是那个十字架上的
救主,而是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上帝。这就是经院哲学最后的走向,由此开始了人
的理性启蒙的进程。与亚里士多德合流的经院哲学使用一种独白语式,一种与对
话和祈祷无关的语式,这一语式起初还能维持它的形式逻辑的论证办法从而维系
着思想的平等,到后来被某种独断论和思想等级制取代。在莱布尼兹、斯宾诺莎
和笛卡尔那里,这种趋向日渐明显。在近代启蒙哲学中,对抽象形而上学法则作
用的无限信赖,对通过理性设计达致应然状况的乐观情绪,对真理可能的负面效
应的不自觉,致使哲大家不再用隐喻和修辞并自以为是诚实。
启蒙哲学依据进步原则将那些设计理性主义的思想视为先进和真实,而把不
承认理性至上权能的思想视为落后和愚昧。设计理性导致的抽象形而上学原则,
变成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车轮,从千万活人的身体上碾了过去。
柏克的警告没引起大家对理性和真理血腥性的警惕,反而连英国国内的绅
士们都视这种警告为精神错乱。真理继续大获全胜,作为拿破仑的哲学化身,黑
格尔胜利地演绎出了他那一套包容所有却唯独容不下真实的个体的的哲学体系。
抽空了偶在个体的辩证法,将它他所有观念全部置入其中,并按辩证的等级
给予分别的批判和定位。辩证逻辑自居于形式逻辑之上,不受形式逻辑批判,人
在这种逻辑面前已无权提源于己的建议,由于普通人所能禀有些正常理性遇见这
种“高级思想”只能俯首听命。那种所谓的历史势必性,那种所谓的绝对理念,
不只剥夺了人在历史行动中的自由,而且也剥夺了个体反驳这种学说的思想的自
由。
辩证法是最大的独断论,由于它把自己封为最高的真理,由于它连形式逻辑
都可以不遵守,由于它否认自己的界限。它的私生子,马克思的学说在社会历
史层面贯彻了黑格尔的这类意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文本
中,马克思将一种建基于思想等级制(意识有真实和不真实形态之别)之上的批判
或不如说嘲讽文风发挥到极致,从而抛弃了思想平等所需要的冷静、客观、平和。
其历史结果是造就了独断论与权力的结合形式——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的
等级制变成了现实的阶级划分的等级制,文本的嘲讽为成了行动中对人的尊严的
蔑视和侮辱,赤裸裸的辩证法娼妓再一次取得了历史嫖客的垂青。
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压迫下产生了反抗者,克尔恺戈尔看清了这种独断论的真
实面相,也看清了它对偶在个体的无视和抽空。作为反叛,克尔凯戈尔在一方面
回到苏格拉底传统和福音书传统,用寓言、对话和复调结构的写作来解决独断论,
把自己从文本中隐藏起来,使读者免受作者看法的强制;其次,他又回到了
祈祷语式对偶在个体的关爱,用一种布道的语言从势必性手中夺回不可能。其结
果是他进步出一套存活的辩证法,它诉诸个体的感受力,强调个体在存活悖论中
的决断。
这种强调个体风格的写作在尼采那里得到了进一步推进,尽管尼采比克尔恺
戈尔要阴险、毒辣。他用一种好像极为真诚的语调使大家疏于防范,并在大家丧
失戒备之际戴上面具,在文本中下毒。他的隐身理由恰好与柏拉图相反:柏拉图
是为了不伤害政治社会赖以维系的信念纽带而不能不用修辞,防止真理被不适
合听到真理的人听到;而尼采则是为了故意摧毁平等年代赖以发生之现代常识分
子理念,他对自己学说某种层面上的公开好像早有期待和预料。尼采进步了一种
反面隐微术,不需要修辞隐秘而用个性化修辞来表现自己的诚实,借以骗取大家对
他的信赖。如此,格言体风格以其敏锐、锋利且更易使人中毒而得到了尼采的青
睐,对体系的反叛使他得以空前地拓展哲学主题的疆域,拓展一种实验性的、细
节更丰富的考虑,从人类生活的所大概的方面颠覆他不喜欢的基本价值法则。
(见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
传统思想的终结在海德格尔的诗性风格和德里达的修辞风格那里得到了最为
形象化的表征。前者试图用诗的语式来扭转形而上学真理的语式,从而达致思与
诗在语言中的近邻关系的彰显;后者则使修辞承担起使文本意义在互文和悖论中
不断延宕其达成的目的,从而展示形而上学真理的限度和言说的困难。在海德格
尔后期的运思中,诗性风格更多地是引入了一种听觉,在听觉中一个空间现身
(“风入于耳,化为四方”)。而在德里达那里,修辞形成的言说时的口吃和句
子的拆分最后指向一种古老的语式:一种隐秘然而是不间断的祈祷。
真理能否公开?
当耶稣教会大家“真理使你们自由”时,他是不是是在说因此真理就能而且
应该向所有人公开?但为何他讲话又要用比喻,并说这是“只叫你们了解,不
叫他们了解”?柏拉图著作为何要设置那样多隐喻,好象他并不想大家真地知
道他想怎么说似的?尼采说话为何时而坦诚得好像要把心掏出来给大伙看,时
而又吞吞吞吐吐,象在故弄玄虚?这类问题引发着大家对真理是不是适于向所有人
公开的考虑。
公开内在地意味着明示方法,而隐秘则意味着不让一部分人了解真理,它暗
示真理具备某种危险性。可怕的或许还不是那种因对真理公开危险的不自知而导
致的对真理的毫无遮掩的、赤裸裸的表达,而是洞悉这种危险后的明诚实欺的真
理表述(如尼采那样藏在坦诚的面具之下)。因此大家需要在这里仔细分辨思想
家们使用隐偏方式的缘由,看看启蒙到底存在什么危险。
用修辞和隐喻的原因,除去出于前述隐秘风格与思想本身内容的关联(赫
拉克利特、海德格尔和《圣经》)以外,大伙可能第一想到的是防止受迫害。这
的确是缘由之一,柏拉图风格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来自于苏格拉底之死。但大家同样
有理由相信思想家们对真理的信念和道德勇气使他们不受这种一般性恐惧的影响,
他们对真理的隐秘一定有更要紧是什么原因,正如柏拉图从苏格拉底之死中得出的绝
不止是政治社会对哲学的害处。大家想到的第二个回答是这是作者的个体性情
所致使的风格,思想沿着适于他性情的方向从个体口中流溢出来,作者可能天生
喜欢隐喻风格,可能天生爱将思想维持在一种秘密的光辉之中。这一回答的不足
在于没办法讲解那些非个性和套路化的修辞办法在海量古典著作中的出现。第三个
回答更带有文学性,可以卡内蒂的话来概括:“在文学中留下很多未说出的事物
是要紧的。如此才大概分辨在多大程度上一个作家所了解的多于他所说的,这
样他的沉默就不是阴郁而是智慧的标志了。”(《钟的秘密心脏》)然而一个爱
智者真的看重的是真理本身的显现,而非自己高明的显现,没理由觉得那些伟
大思想家如此做只不过为了证明自己有智慧,思想的彻底和明晰性的需要不允许他
们把自己的智慧凌驾于真理本身之上。因此,大家还需要从从真理的特质、社会
的基础和人性的倾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考虑为何要隐秘。
为何会有(批判性)真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能够帮助大家看清真理的本性。
一个社会的基础是一套基本同质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是经过多年选择
和修补的结果,因此它对于应付将来的不确定性和维系社会的有关性有可验证的
效力。
问题在于,这种价值体系同时也会是路径依靠的结果,亦即事实上是在选
择的线性时间的不可回复性中锁定的劣等均衡。如此,传统的不完备性使得怀疑
成为必要,那些不拥有自我怀疑和修正能力的传统都已被或将被历史淘汰,因而
存活下来的传统本身就包括着其中个体的怀疑能力。其次,人的形而上学天
性促进人努力要弄了解他自己的存在,它每时每刻不在质问事物和世界秩序的合
理性,质问大家同意的传统信念的正当性。真理来自于个体逃离洞穴的愿望,它以
寻极究底、不屈不挠的彻底性为其特点,象普罗米修斯那样无视天上的诸神和人
间的偶像,就算它的结论直接威胁到人类生活的基础。
如此,真理的特质在于它关涉社会的基础,它的逻辑彻底性致使它常常能说
服人,从而获得一种百压不屈的传播力量,这种传播就大概对社会赖以维系的
信念根基构成风险,恰如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思想的反应所显示的那样,应该把
苏格拉底之死看成是雅典的自卫。这种政治和哲学真理之间深刻的紧张不可以使用
一种一边倒的方法作出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关涉到人类生活的内在秘密和悲剧
性特点。社会的基础,在于不可以被深究的建议和信念之中。这类建议和信念构成
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构成人与人行为预期的形成要点,个体正是在这种预期体
系中才获得他的安全和生活的可能性空间。个体固然有探究真理的天分的自由,
但他作为公民同样要因受益于规范和传统而承担起对规范的责任,这正是苏格拉
底之死的真的意谓。
从更细节的层次看,思想来定是“还在路上”,并且理性有它天然的界限
(常识论上的),人类生活自己的丰富性不可以完全被理性和逻辑化,因此思想来
定不可以失去对自己的检讨和限制,但它的传播和社会化过程恰恰就是思想失去
深思性的过程。这种丧失深思品格的思想容易堕落为一种失去具体语境的抽象原
则,并且容易忘掉自己的不完备性,因而其无限制的传布会对社会及此种思想本
身产生很大的害处。因为真实的思想会对作为社会基础的价值体系提出质疑,
而且它的否定的部分也确实有很大的真理成分,因此在逻辑上说它动摇了社会
的存在基础。而假如这种思想碰到那些生来就不太会深思的激情者,逻辑上的可
能性就会变成现实性。但基本上所有些思想在其否定部分的有效性都不可以变成其
一定部分的有效性,因此在动摇社会基础之后如何重建一个新世界的基础就很
困难。这就是迈蒙尼德所说的,有的人生来就不合适听到完全的真理,他们会被
真理所误导,导向谬误和混乱。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出于对真理的热爱
而是出于一种借助的目的向社会传布思想,被他们传布的思想一般与原思想毫无
关系,但不可以不承认思想本身也应付此负责。
因此,一种思想在表述自己时应该注意克制,克制自己的极端化倾向,努力地
使表述更温和和审慎,把自己的锋芒藏到只有少数人能觉察的地方,以防止它被
某些人误解和借助。同时,在关系到对社会基础的质疑时,不只要永远维持对这
种基础的同情的理解,更要紧地是在表述中尽可能防止正面直接说出此种否定。为
此在著作中要用种种办法,如修辞、隐喻、类比和非常重要的对话式办法(柏拉
图的辩证法正是为了防止使思想变成一种说教和灌输的单向运动,防止读者失去
独立考虑的能力)。这并非害怕社会的迫害,更不是自私,而恰恰是担忧自己
的发现会给社会导致风险,是预先防范真理的负面效应。这一点在风险性极高
(一项学说大概破坏整个社会的均衡)的现代社会中应成为每一位学者的基本
责任。
真理的负面效应还表目前,一些真理,特别是关于人性真相的思想,假如不
加克制地表述出来,会使那些无力承受的人绝望,由于即便是思想者自己也未必
有承受的力量。无论怎么样,大家思想的目的不是使更多的人绝望,就算大家自己
早已绝望。这个世界上有力量达到信仰的人少之又少,而只有信仰能救人于绝望,
所以在这个神蚀的世界,要永远克制思想的过于黑暗的进步。现代思想中有一极
基本上是在重复《传道书》中的话,但它却并没《传道书》解决虚无问题的上
帝出现。并非所有些人都有承受真理导致的绝望的力量。因此,思想在表述这
一部分真理时也应该注意隐秘。
除此之外,隐秘还有一个相当要紧是什么原因,即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
传奇中所揭示出来的人性的实情。甚至在上帝重返世界之时,人类也仍然是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是强有力的(在精神上),他们勇于思想,勇于成为自由
人;另一部分则相对要柔弱,他们没太多的力量考虑,也无力承受太多的自由。
因为自由也是一种重担,思想也是一种苦役,因此上帝在造人时就天然地把考虑
的任务交给了前者。假如你告诉后者他们可以自由思想了,他们会惊恐地舍弃这
种自由并将这类自由归还给你。自由将使他们不会幸福。或许大家可以将他们的
生活称为“伪生活”,甚至傲慢地宣称他们的理想是“猪栏的理想”
,但在上帝眼里这也是真的生活的一种,由于他们天性这样,他们也是上帝
的造物。思想应该是为大部分人的幸福着想的,而他们正是大部分,他们不期望
有人给他们完全的自由和赤裸裸的真理。因此,在争取到政治经济自由和平时生
活的自由之后,他们无需另外的自由。在此时,假如大家过分直率地将他们的
不自由境况告诉他们或纯真无邪地想让他们自由,他们会失去旧有些幸福和欢乐。我
们需要对他们守旧某些东西,就象宗教大法官守旧了天主教一直是按撒旦的原则
行事的秘密。这并不是可以让大家感到优越的事实,而恰恰是让大家悲哀的事实,
由于大家不能不在某些时候向谎话妥协,不能不残酷地看到人类社会达到乌托邦
境界(所有人都完全自由)的不可能性,不能不承受大家自己的虚伪和隐瞒的罪
过,虽然是为了不伤害更多的人而犯下的罪过。
正如列奥。斯特劳斯所言,政治和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说需要一些不可追究
其合理性的原则,以维系其公民的忠诚和热情,维系他们的相互关系,维系他们
对自己幸福的理解;而思想,在本质上出于一种逃出洞穴的需要,是要弄了解我
们自己存在的努力,它每时每刻不在质问事物的合理性,质问大家我们的幸福观
念,它试图在大家身上打造一个城邦以抵抗肉体的朽坏。因此,对世界负责的思
想者在思想的同时也势必会尽可能隐藏思想的面目,防止大家在看到它时变成石头。
启蒙现代性与回到隐秘如前所述,哲学与政治,或求真意志与社会责任的紧
张在思想者那里表现为,对于这一社会的传统及政权的合法性,我需要维持必要
的敬意和同情的理解;其次,我又不可以舍弃批判地审视它的见地。二者的均
衡在康德看来,意味着作为政治社会(国家)的一名公民,我需要服从法律和道
德,并支持这个政权的统治(只须它不是公然践踏自然法的);而作为人类社会
(理性)的一员,我又需要在理性的公开运用中质疑法律、道德和政权的合理性
(《何谓启蒙》)。康德试图以这种双重性来推进理性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力
(启蒙),同时平衡理性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对启蒙的限制)。然而,事情在
这两个方面的复杂性可能都超出了康德的想象。
我将现代社会划分为四个层面:个体空间,契约空间,公共空间和国家。
在个体空间中,个人遵循其性情伦理和美学法则的引导,以维护其私人范围
的独立和尊严;在契约空间(包含家庭)中,买卖双方遭到市民法典(民法和商
法)、互定契约和买卖习惯(包含家庭道德)的制约;在公共生活(社团、政党、
平台和学院讲座等)中,个体遭到公共道德、社团或学术规范及自己良知的限制
;在国家里,人的行为受公法的调整。那样,私用理性的运用实质是在国家和契
约空间中发生的,公用理性则在公共日常得到发挥。但这只涵盖了四度空间中
的三度,还有个体空间未受涵盖。因此,在这里还有一个个体以什么作为自己心
性伦理和在体特质的问题。而福柯的启蒙恰恰是针对这一范围的,也是他超越
康德之处。古典自由主义在康德那里得到的理性主义讲解及其在英美学者那
里获得的经验主义辩护力量的确极为强大,使“在传统的边际进行革新”好像已
成为知识,但它有意无意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亦即个体的自由的实质而非形式
要件是个体不受别人支配的独立判断力和存活方法的独特质。古典自由主义的自
由最多只不过平时生活和政治的自由,而不是精神和存活论意义上的自由。这一点
柏林在《自由四论》已讲得很了解。而对于精神自由而言,一个公正自由的政
治规范并不是充要条件。因此,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关于异化的部分到今天仍未失去
时效性。一个民主社会中,人可能异化为毫无独立判断力而受制于大众趣味和某
些专家建议的存在,那些千篇一律的美学法则将造出一大量伪个性主义(没反
思和内在稳定性的贪新鹜奇)和伪生活;而一些特殊一同体也将被同化而失去自
身的文化特质(这一问题即是“承认的政治”问题,本文将不涉及)。
基拉尔的《浪漫的谎话与小说的真实》中指出了这种异化社会中人的存在状
况,个体的自我认可从倚赖于一种较为稳定的传统向倚赖于一个受制于意象形态
(昆德拉《不朽》)的大众和别人转化。社会在依次历程统一的风俗装束、宗教
颁布的道袍装束和国家定制的制服饰束后,将由不断变幻的时装(意象形态)设
计师设计的时髦装束统辖每一个个体的存活,而个体却还以为这件时装体现了他自
身的曲线i.在对虚荣的现象学- 历史剖析中,个体对自己个性的幻觉全方位崩溃。
而个体的自我认可从自由的本意来讲需要是自己考虑的产物,是一种自我斗
争和自我辩驳的结果。而信仰,就是此种自由的最高体现。真实的信仰,按克尔
凯戈尔所言是一种“无限弃绝”,是个体之不可能的可能性,也是超出虚荣机制
的唯一路径。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假如没高于个体的价值,就不会有个性
;假如它只是高于个体的价值之方法,也不会有个性。”(《箴言》)
因此,启蒙在现代性语境中至少有如下四种含义:对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
平时生活自由的争取(古典自由主义);对法律和社会价值体系的质疑(理性主
义);对个体面临的“阱架”制约的越界(马克思式的社会整体层面上的越界和
福柯式的个体存活方法层面上的越界);认清自己的虚荣本质和对虚荣的超越
(信仰)。这种多重歧义显然不是用康德“敢于运用你一个人的理智!”就能说清
的。
那样,在对启蒙的限制上,康德的办法又起了什么用途呢?启蒙哲人关心的
不再是在自己身上打造一个城邦,而是要在人类社会打造一个理想城邦,让他们
在现存秩序中变得驯顺显然是不现实的、诉诸应然性的空想。不是有那样多哲人
亲自拿起枪反对现存秩序吗?密尔《论自由》寄望在自由民主规范中以思想与思
想之间的辩驳来制衡一种思想可能具备的负面效应,但到了现在恐怕也是事与愿
违,不只在思想界从未打造起一种较为稳妥的秩序,反而致使相对主义的横行及
其对人类生活的戕害。启蒙的最后收获是思想和现实的相互残杀:现实被观念的
独断送进极权的地狱,或被观念的相对主义送进绝望的深渊;而思想被现实的需
要简化和歪曲,或被现实的功利性所鄙弃。
启蒙话语在近现代的不断推进使得隐秘传统被中断,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
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福柯主义还是基拉尔主义,它们都倾向于将世界和人性
的基底以一种独一无二的明确性揭示出来。即使在康德那里出现了对启蒙的限制
也并未使事情产生任何改观,由于康德的公用理性的表达也未运用任何隐微之术。
甚至那些认识到隐秘传统存在的人,在他们的论著中也不能不用启蒙语式将
隐秘传统揭示出来(如列奥。施特劳斯),而本文的言说虽旨在呼吁回到隐秘,
却也使用了启蒙语式。隐秘传统的中断加剧了现代社会的风险,常识分子对于其
言论自由可能导致的害处毫无知觉(这一点在汉语思想学术界中尤为明显)。也
许有必要在此重温列奥- 斯特劳斯的训戒:从来不会也不应该有哲学家的言论自
由。
尘世生活的最高目的,在我的理解中,是自由而平安。自由意味着不受强制,
包含各种不正当的权力支配关系(如意识形态、意象形态和各种常识话语)的强
制;而平安意味着对现存秩序的珍视,与在这种秩序所给出的私人空间中的坦
诚和安宁。
启蒙虽然揭示了各种权力支配关系的存在,但它本身作为一种常识话语构成
了对人的强制,它也会会与权力形成新的同盟关系;并且,它对秩序的挑战威
胁到人的平安,把人置入一种危险的自由之中。危险对人当然永远有魅惑力,因
为它迎合了一部分人冒险的天性,但为了满足自己冒险的欲望就把整个社会和他
人推到危险和混乱之中未免过于自私。不可以需要所有些人都“在高山之巅和冰雪
之间生活”。隐秘传统作为一种真理言说方法,它是哲学家身体上的城邦与现实
的城邦之间订立的契约,有效地保证了人类的自由和平安。
市场意象形态对人的任性的鼓励,在今天蔓延到学术与思想之中,回到隐秘
传统看来纯属我的一厢情愿,何况语言功底的常见退化使学者们已无力使用
隐微术。但我仍然抱有期望,对于思想者责任心和尘世生活前景的期望。隐秘继
续说着一种边缘和孤立的语言,它虽然微弱,但却象黑暗一样守护着事物内部,
抵制着启蒙之光的侵袭,而言说者也得以在此抽身而去:“向所有人隐藏自己,
为了让某个人找到。”
一行2000年9 月20日于武汉
i 衣装的意义只能在个体身体同别人目光的关系中得到适合的说明,一种衣
装就表明了一种存在方法,表明了这个个体对自己身体的安置和对别人目光的理
解。这个别人可以是单独的个体(如情人),也可以是一个小圈子(朋友或家庭)、
一个阶层(如上流社会)、甚或整个大众(时髦)。个体身体所朝哪个方向的打开对象
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个人的个性的真假,由于身体比灵魂更不容易作伪。甚至在那
些极端的衣着形态(破衣烂裳或裸身)中,所表现出来的也并不止是对自己身
体的蔑视、忽视或自我陶醉,而是对别人目光的依从,由于证明自己比别人目光
高明本身也有赖于别人目光;而人只有在对别人目光的征服中才可能自我陶醉。
刘小枫的时装现象学只注意到了个体身体自我确证及其颠覆永恒理念的方面,却
忽视了别人目光这一至关要紧的维度,没看到是别人目光而不是个体身体的自
我感觉在时装表演中的最重要地方,没看到即便是永恒和不朽观念在现代也变成
了一件衣装,可以看作是破旧的反时装,也从反面依从于别人的目光(见昆德拉
《爱德华与上帝》)。身体感觉的本体论是现代学术神话和个体所能拥有些最大
幻觉,由于它向个体(也向研究个体的学者)掩蔽了个体存在并无独特质的真实
面相。在这一年代,个体的自我认可并不是基于对自己本质和内在稳定性的理解和
坚信,而来自以别人目光为中介的重构,个体的自我想象以别人对自我的想象为
参照系。在上帝、真理和乌托邦消失之后,人类将为别人的目光而奋斗,现代所
有些基要定义:财富、声名、不朽、权力和性爱都要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
是的,即便是在前现代时期,大家也不可能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目光,但那时
大家所在乎的是大家所尊重、所爱的人的目光。别人是作为与自我有质的差别的
参照系存在的,他们有更高的威望、默契和天惠让大家相信(如对族长、对亲人、
甚至对上帝的目光的敬畏)。
而现代市民社会的生成致使一个无差别的大家的兴起,他们的判断力与大家
自己一样毫无内在稳定性。昆德拉《生命中不可以承受之轻》剖析了人所存活于其
下的别人目光的种类:第一种是生活在自己所熟知的人的目光之下(如弗朗兹的
夫人);第二种是生活在很多不知名的目光之下(如演员);第三种是生活在一
双远方的双眼之下(弗朗兹、西蒙,还有真的的信徒们);第四种是生活在自己
所爱的人的双眼之下(托马斯和特丽莎)。你看重什么样的别人的目光,你就如何
存在。
隐秘与启蒙——论真理的语言形式
点击数:115 | 发布时间:2025-03-05 | 来源:www.rrf53.com
- THE END
声明:本站部分内容均来自互联网,如不慎侵害的您的权益,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
-
- 学习交流 -
-
欢迎加入中国人事人才网,与万千考友一起备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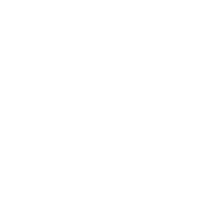
- 成考路上不再孤单
专业院校
-
关注“考试直通车”
-
领取备考大礼包
-

点我咨询
返回顶部
Copyright©2018-2024 中国人事人才网(https://www.xftgo.com/)
All Rights Reserverd ICP备18037099号-1

-

中国人事人才网微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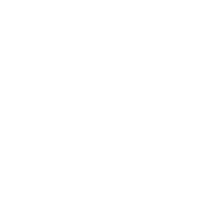
中国人事人才网